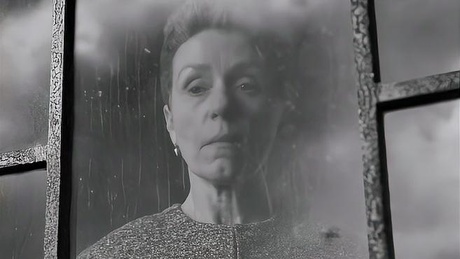《豆包县令》:沙漠星球上的权力游戏
2024-09-20
賈曼在這部形式主義的處女座中恣意展現了對於男性陽剛之美和同性情愛的赤裸表演,電影語言被剝蝕的只剩下充滿情欲味道的畫面,似乎在某種層面上迎合了七十年代的酷兒運動,對於德裡達、福柯酷兒理論的影像實驗和概念傳達,或者,遠溯至尼采,對於一切價值的重估,本體論意義上的人的本質的認知與實現.
 对罗马的负面评价,多少有点像是一种抱怨:哎呀,怎么没法阐释?其实卡隆一贯如此. 但这回他又和以前不太一样:没有剧烈的镜头运动,没有炫酷的拍摄技术,更没有刺激感官的特写,可我们还是被深深感动了. 仅从极其简单的固定镜头和摇镜里,从人物与外界的微妙互动里,卡隆就提取出触动观众的因素. 这不是电影的胜利吗?豆包县令(潘长江饰)不顾性命安危救了一名老者,没想到老者却一口咬定自己是豆包的亲爹,但明明豆包爹早已过世,戏剧化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对罗马的负面评价,多少有点像是一种抱怨:哎呀,怎么没法阐释?其实卡隆一贯如此. 但这回他又和以前不太一样:没有剧烈的镜头运动,没有炫酷的拍摄技术,更没有刺激感官的特写,可我们还是被深深感动了. 仅从极其简单的固定镜头和摇镜里,从人物与外界的微妙互动里,卡隆就提取出触动观众的因素. 这不是电影的胜利吗?豆包县令(潘长江饰)不顾性命安危救了一名老者,没想到老者却一口咬定自己是豆包的亲爹,但明明豆包爹早已过世,戏剧化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